專訪畢可思 (Robert Bickers) 教授
|
|
畢可思 (Robert Bickers, 1964-) 教授,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Bristol University) 歷史學系教授 (Professor of History),歷任人文學部研究副部長,現任助理副校長(專責研究生事務)。正如中研院近史所「西學與中國研究群」 2020 年邀請其為年度訪問學的介紹:「他以英帝國史和殖民史的角度出發,研究近現代中國的英國人團體,特別關注外國人在中國的相關活動,例如:公共租界、租界、租借地、英商公司、英國國教傳教士與中國海關等,其所出版關於英帝國從晚清以降在中國激出的民族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的殖民特徵等專著,已經成為此領域的必讀之作,對非正式帝國理論有進一步的擴充和修正,也對於英帝國在中國的擴張進程提出深刻檢討。」畢教授以歷史中游移在兩個文化間之個體生命史來觀看大歷史的進程,開展出一系列視野獨特的歷史寫作,此次訪談可透過畢教授的學思歷程,看到歷史學研究與個人生命史之間豐富的互惠與互動。
畢教授自 1992 年取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博士學位後,先後於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與研究員,並曾任職於香港大學人文學院,1997 年起開始於英國布里斯托大學任教。畢教授長年以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國的英國人團體、外國人在華的活動,以及中國近代化的歷程,其著名的著作包括《英國人在中國:社群文化及殖民主義,1900-1949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 ,1999)》、《帝國造就了我:一個在上海漂流的英國人(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2003)》、《瓜分中國:清帝國中的洋鬼子,1832-1914 (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 2011)》、《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 (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 , 2017)》等。除了學術著作的豐碩成果外,畢可思教授也曾擔任牛津大英帝國史系列的編輯,並致力於推動中國歷史相片數位化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digitisation initiative),以及中國海關史研究計畫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project),對於大英帝國與中國的近代關係史研究資料的整理與推動不遺餘力。
他 2020 出版的新著《躍向中國:太古集團和它的世界,1816-1980 (China Bound: John Swire & Sons and its World, 1816-1980, 2020)》,則是奠基於既往研究的關懷之上,此書以香港太古集團 (John Swire & Sons (HK) Ltd.) 的發展史為主軸,探究一個企業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如何透過貿易串連起中、英兩國與世界的關係,使地域性的經濟往來交織成全球貿易的網絡。綜觀畢教授至今的學術成就,可以知道他長年持續關注近現代中國的遭遇與變遷,而如此的學術傾向是如何產生的?或許與畢教授身為英國人的身分,以及豐富的旅居經驗有關。
和中國文化的緣分:旅居香港與臺灣
畢可思教授 1964 年出生於英格蘭西南部的威爾特郡 (Wiltshire),從小由於父親工作之故,時常跟隨家人旅居各地,除英格蘭外,他也曾隨著父親旅居德國和香港。據畢教授的描述,約莫六歲時,他與家人一同搬往香港的英國皇家空軍基地 (Royal Air Force bases),直到九歲才返回英國。在香港的特殊經驗,對畢教授來說雖然是一段塵封已久的往事,但他憶及當時初抵香港從啟德機場進入市區,沿路所聞到的氣息、所見的顏色,甚至聽到的噪音,都和英格蘭冬天濕冷的氛圍形成鮮明對比。這樣的感官經驗讓當時初次來到亞洲的他備感新鮮,至今回想起來依然記憶猶新,而這也是畢教授首次與中國文化相遇的時刻。
在香港三年後,畢教授又返回英國。在十二歲時,同樣因父親工作的需要,與家人再次離開家鄉,前往德國短居一年後返回英國,之後才真正在英國定居下來,並在英格蘭南部小鎮的寄宿學校中完成高中學業。畢教授在寄宿學校的求學過程雖不似先前四處漂泊,但是對於偏好靜態活動,特別是熱愛閱讀的畢教授來說,並沒有因此適得其所。畢教授的興趣在這一所致力於培養運動員的校園中顯得格格不入,也因此在寄宿學校長達五年的求學時間,對他而言並不是特別愉快的求學歷程。所幸當地小鎮上開設的一間二手書店,成為他當時寄託心靈的最佳場所。或許是香港的三年旅居經驗在畢教授心中種下了探索中國的種子,在二手書店裡有著為數不少英譯的中國文學書籍,成為其進入大學之前認識中國文化最重要的養分。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讀物為企鵝出版社 (Penguin Books) 出版的企鵝翻譯和企鵝經典系列叢書,畢教授透過在二手書店的大量閱讀中,接觸到中國文學。
畢教授結束高中生活後,進入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就讀。他原先主要修習中文研究 (Chinese Studies),以今日來看是屬於中國語文學系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的課程。不過畢教授不諱言的說,以他當時的程度學習中文非常困難,因此即使他已經非常認真的學習,第一年還是未能通過系上語言方面的評測,因而喪失隔年前往中國學習的機會。面臨此一挫敗的學習經歷,畢教授毅然地轉至他更為擅長的歷史學系,然而因應當時校方的規定,需延遲一年才得以轉系就讀。無法無縫接軌的轉系過程讓畢教授多了一年的空閒時間,畢教授決定好好利用這一年面對令他挫折的中文,於是他隻身來到臺灣,藉由教授英文賺取生活費,同時也在國語日報社努力學習中文。在 1980 年代的時空環境下,倫敦尚無太多華人活動,也缺乏訓練中文的環境,因此在臺灣的經歷讓畢教授能夠更快地掌握中文。也正是經由在臺灣生活的一年,奠定了扎實的中文語言能力基礎,使得日後中文成為畢教授研究近現代中國的一項優勢。經過一年在臺灣的學習後,當畢教授隔年再次回到大學,便順利的通過歷史系資格考。畢教授對學習中文的熱情並未因轉系而止步,他就讀歷史系期間,也從不間斷地精進中文能力,無論是語言學習或是旅居香港與臺灣的經歷,都幫助他在未來的研究中更深切地探索「中國」。
望向中國:從英國的角度踏上研究中國之路
有趣的是,理解、研究中國有各種方式與時代的選擇。從畢可思教授的著作來看,他持續關注現代中國史,且是以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作為研究角度,這樣的研究取徑與他在博士論文研究的選題息息相關。然而,畢教授並非一開始就毅然的投入此研究之中。在選擇博士階段的研究領域時,畢教授曾經考慮以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早期現代英國和十九世紀的法國作為研究對象。然而,這兩個領域對拉丁文和義大利文要求極高,因此,擅長中文的畢教授轉念,思考是否有研究中國的可能性,並在文化交流與互動的議題上研究中英關係。畢教授還記得,當時在亞非學院圖書館中看到過一本名為 How England Saved China 的書籍,書名引發了他對英國人眼中的中國是什麼樣貌感到好奇,並試圖理解在英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如何變遷。於是畢教授將博士階段的研究重點,放在二戰時期英國對中國的印象這一研究議題上,進而理清中國在英國人的理解中,如何由十九世紀以來的負面形象轉變成正向的歷史成因。在畢教授博士論文決定以二戰時期作為研究的斷代時,也正值英國檔案的三十年保密條款 (Thirty-year rule) 鬆綁,使得很多檔案與歷史材料得以公開。畢教授一開始由外交史的角度切入這些史料,而後漸漸從中發現中國形象的轉變不僅僅是因為變動的二十世紀所產生的歷史現象,更與大英帝國殖民史息息相關。於是畢教授的博士論文以「英國人對中國及中國人態度的變遷,1928-1931 (Changing British attitudes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1928-1931)」為題,研究取徑也一改以往學界專注於歷史文本解讀的方式來研究英國視野下的中國形象,轉而以在華通商口岸的外國人社群為關注焦點,進行社會經濟與文化等面向的考察。畢教授的第一本專著《英國人在中國:社群文化及殖民主義,1900-1949》(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即奠基在其博士論文之上發展而成。
畢教授研究取向的選擇與 1990 年代歐美中國史學界頗為不同。當時在英國,多數對中國的關注都聚焦於古代,很少有學者研究現代中國。當時的亞非中心也沒有中國或是東亞等更細緻的分類,只有畢教授等少數幾個研究生鑽研此領域。也由於研究領域的差異,畢教授並不被英國的中國研究學界視為學術網絡的一部分,反倒是美國的中國研究群更能與其研究的內容產生對話。因此,畢教授多次參加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康乃爾大學的學術會議,將其研究成果和美國學界分享。也許是畢教授自身與學術界連結的經驗使然,他還發起了一個名為 “China postgraduate network” 的計畫,旨在聯結英國研究中國相關領域的學者,現已易名為 “British Postgraduate Network for Chinese Studies (BACS)” (http://bacsuk.org.uk/bpcs),至今仍持續運作。
英國學界當時較少關注現代中國研究的情況,也一度影響到畢教授求職。當畢教授應聘布里斯托大學時,招聘委員會曾質疑畢教授的適任性,因為他們認為,當時布里斯托大學並沒有和畢教授所研究內容同領域的學者能與之交流。畢教授則用不同的角度回應這樣的質疑。他表示,他的研究取向關係著中、英兩國的歷史現象,因此他不但可以藉由社會網絡和中國的研究人員進行相關的研討,也可以和英國其他的歷史學家交流。畢教授的回答,讓他開啟了中國史與英國史更廣闊天地與雙方交流的可能,也讓當時的委員會折服。於是,畢教授順利於 1997 年任教於布里斯托大學,直至今日。
畢教授研究範疇不僅限於現代中國跨國的歷史研究,更有跨域的研究成果。他在完成博士論文後,曾於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 (Nuffield College) 擔任博士後研究。在此期間,他運用修習博士期間廣泛接觸的第一手資料,將其中有價值的材料陸續轉化成研究成果並在期刊上發表。畢教授所發表的第一篇期刊論文是作家老舍 (1899-1966) 的研究,該篇文章並非刊載在歷史學相關的刊物,而是發表於文學期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也由此可見其研究興趣與領域之廣博。
殖民中的個人與民族主義的發生:開展研究中國的雙重視角
畢可思教授在牛津大學博士後研究期間,也為其計劃的第二本專書搜集材料。畢教授進一步將目光轉移到大時代中的個體人物上,例如在上海工作的英國官員,以及溥儀的老師莊士敦 (Reginald Johnston, 1874-1938) 等。並透過這些看似只是個人生平的相關史料作為切入點,發現更大的歷史拼圖。從小人物看大歷史的研究路徑,也影響了他搜集二十世紀英國在華僑民資料的方向。畢教授曾赴位於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 (Imperial War Museum) 收集相關研究材料,畢教授回憶道,當時的館員遞給他兩盒檔案,並說:「我想你會喜歡這些東西的。」這兩盒檔案由上海警察理查德.廷克勒 (Richard Tinkler, 1898-1939) 的妹妹寄放在該博物館。畢教授從這些檔案中,將一個粗暴、有流氓氣、愛炫、種族主義而又能幹的上海警察——理查德.廷克勒從歷史情境中還原出來。經由畢教授的研究,理查德.廷克勒這個歷史中的小人物變得清晰可見,他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結束後到上海,轉業成為警員,而後由於酗酒而自毀仕途,1939 年被日本軍隊刺死,結束了他的一生。理查德.廷克勒的經歷在畢教授眼中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生命故事,更讓學術研究中性別、帝國、殖民主義這些抽象的學術名詞,都具體的在這個白人工人階級身上體現。畢教授為了追尋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還曾多次到上海檔案局,試圖翻閱當時僑民的個人檔案,而這個看似歷史中的小人物,也成為畢教授第二本專書:《帝國造就了我︰一個在上海漂流的英國人》(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的主角。
畢教授在第二本專書成功出版後,隨即接到企鵝出版社的提議,希望畢教授撰寫一本時間跨度更長、視野更廣的英國人在華史。應出版社要求,畢教授第三本專書以《瓜分中國:清帝國中的洋鬼子,1832-1914》(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 為名,於 2011 年出版。此書是以第一個抵達上海並創辦了十九世紀重要洋行——Lindsay and Company of Hong Kong的英國人:胡夏米 (Hugh Hamilton Lindsay, 1802-1881) 為主軸進行歷史敘述。畢教授發現,胡夏米的例子並不像過去研究中國歷史的史學家所認為的:十九世紀中國處於一個歷史衰弱的階段;相反的,當時中國洋行興盛的情況是外國洋行難以匹敵的。此外,經由畢教授的研究發現,十九世紀的中國人在面對新的技術或制度時,都能很快的適應、模仿甚至奮起直追,因此過去將十九世紀視為衰弱的歷史敘述並非歷史的全貌。表面上看似被外國列強瓜分且日漸衰弱的十九世紀中國,其實卻與外國在貿易、技術上有著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並非一味的遭歐洲列強鯨吞。
在完成《瓜分中國》一書的研究後,畢教授對於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後的中國感到好奇,更對現代中國狂熱的排外心態感到不解。因此畢教授出版了另一本著作《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探索現代中國如何建立他們的民族主義。畢教授透過中國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中國的雙重視角進行研究,發現在雙向理解的過程中,有著巨大差異和認知鴻溝。畢教授意在說明,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當然具有國家操控的成分,但是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十九世紀後隨著西方列強逐漸離開中國,帝國主義所產生的殖民歷史並未消失,反而更深植於中國人民生活的各個面向,而這些帝國主義的遺緒更影響了現代中國在面對外國時展現的強烈民族主義形象。對中國人來說,殖民的歷史並不遙遠,就如同畢教授在寫作《滾出中國》時,這些僅僅是在二十年前發生的歷史,它還是明確而清晰的存在著。
研究香港的計畫與展望
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史最鮮活的例子莫過於 1997 年才回歸中國的香港,畢可思教授於 2020 年 3 月出版的最新著作《躍向中國:太古集團和它的世界,1816-1980》(China Bound: John Swire & Sons and its World, 1816-1980, 2020) 一書中,詳細的追索太古公司 (John Swire & Sons (HK) Ltd.) 的歷史。當然,和《瓜分中國》一書一樣,畢教授的關注點並不只是太古公司的商業史,而是藉由太古這間扎根於香港的老牌英資洋行,考察大英帝國如何以香港為基地進行業務擴張,以及建立與中國的關係。透過考察太古這間洋行的歷史,可以發現其歷史脈動就是香港歷史的縮影。畢教授提到,今日位於香港鰂魚涌的中產住宅區——太古城,是香港首個大型住宅建案,其前身就是太古船塢和太古糖廠,而太古城的建造就是一個由大型財團參與都市化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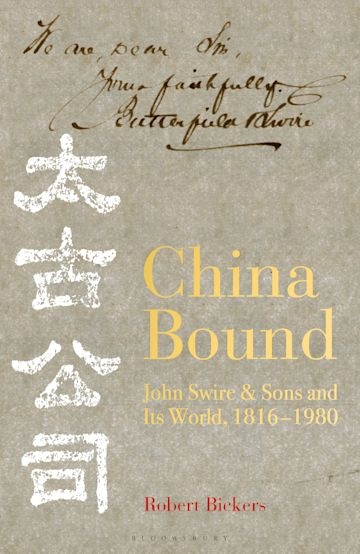
畢教授還談及他近來指導的香港歷史計畫。此計劃緣於香港在 2014 至 2015 年的雨傘運動期間出現的歷史省思,計畫捐助人原先設定的研究範圍較狹窄,在畢教授建議下,才將研究視野放大到所有與香港有關的歷史。畢教授認為,香港的歷史值得進一步發掘的原因,是因為香港不同於任何一個中國城市,它是英國的殖民地,以完全不同的邏輯在運轉。且在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歷史中,香港接收了各式各樣的居民,如:葡萄牙人、馬來人、越南人,甚至非中國人的共產主義分子,這些外國人的來來往往構成了香港的多元性和複雜性,這個研究計畫的推動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且仍會繼續推進。
談及未來的研究展望,畢教授分享了他在海關檔案中發現的一個有趣案例。1932 年,共產主義者占領了汕頭附近的石碑山燈塔,並在撤退時「帶走了」燈塔管理員奕偉士和逐俠諾等人,而後這兩個人又悄然死去。這樣的歷史人物故事就和《帝國造就了我》中的主角上海警察理查德.廷克勒一樣,這兩個人的境遇不僅僅是他們的生平,同時也揭示了英國勢力在中國的複雜情況與多樣性。有趣的是,畢教授還找到了他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後代,但他們彼此之間卻對對方的存在渾然不知。畢教授興奮地表示:我成了他們的連結點!除了燈塔管理員奕偉士的研究外,畢教授也正在進行另一位於 1912 年被英國法院監禁於上海的女性詐欺犯的生活故事。這個故事與奕偉士相同,皆是微觀歷史的研究,透過這些歷史故事主人生命的連結,讓畢教授的研究隨著故事主人公的生命經驗,穿梭在世界史之中。在持續的個案研究之外,畢教授也感興趣於具「創造性」的歷史寫作方式。他在 2016 年與七位研究學者同赴英格蘭東德文區 (East Devon village) 的 Branscombe,透過畢教授所謂的「創造性的位移 (creative dislocation)」,將一群研究者拉離開他們習慣的地方、日常、研究主題、研究方式、甚至個人的寫作風格,重新以經驗為始,認識並參與當地的自然與人文,並嘗試以合作及創造性寫作的方式進行學術討論與發展論文,進而檢視「創造性」與歷史書寫的關係。這個計畫的過程與初步成果已於 2020 年刊載於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
最後,畢教授也回應了對他以微觀歷史進行歷史研究的批評。畢教授認為,歷史本身就是由個人所組成的,因此沒有誰更重要,或者誰比較不重要的區別,而且個人在大的歷史洪流中的境遇和抉擇本身,也是讓宏觀歷史得以具體化的重要表徵。畢教授對於歷史學的興趣從「人」開始,尤其關懷生活在跨界、跨文化中看似平凡的個人。他不僅以他人的生命史作為歷史研究的材料,對於探索歷史學者自身如何看待個人經驗與歷史寫作間的關係也充滿興趣。他所嘗試開發的合作研究與創造性歷史書寫,應該會為我們思索多元寫作時,提供更多靈感與刺激。
[1]關於這個計畫的內容詳參:Robert Bickers, Tim Cole, Marianna Dudley, Erika Hanna, Josie McLellan, William Pooley, Beth Williamson, “Creative Dislocation: an Experiment in Collabo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ume 90, Autumn 2020, p.p. 273-296.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