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四次討論會紀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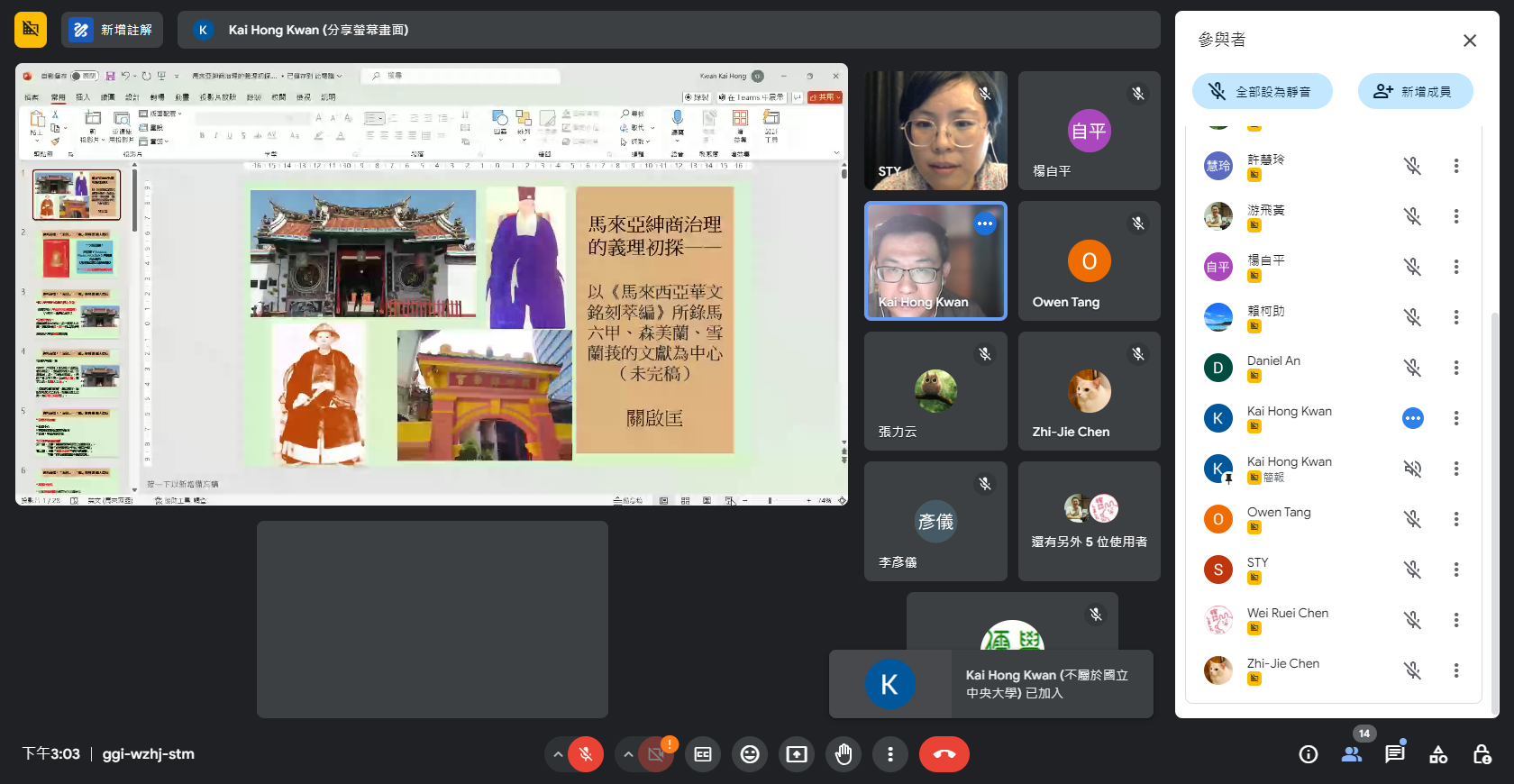
|
關啟匡教授〈馬來亞紳商治理的義理初探——以《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所錄馬六甲、森美蘭、雪蘭莪的文獻為中心〉一文,是延伸自曾經參與過的研究計劃「張弼士任領以來馬來半島北部客家村鎮港口網絡的形成——以碑銘爲中心的研究」的思考。他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間,已完成兩篇葉德來(1837-1885,俗稱「葉亞來」)研究的初稿。今年,他嘗試利用 1980 年代由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 與陳鐵凡合編的《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所錄的文獻,重建自明亡後紳商治理下的馬六甲華人社會所蘊含的儒家義理。這個向度的研究指出,數百年來馬來亞境內的華社存在文化教養的傳統,以及華人領袖的紳商,都能展現出華南原籍所世代承襲的儒家教養意識。19 世紀中旬以降,源自馬六甲州的三多廟,伸展至森美蘭州的雙溪芙蓉,再轉戰雪蘭莪州吉隆坡地區的拓殖部隊「海山公司」,陸續出現盛明利 (1822-1860)、劉壬光 (1837-1885) 與葉德來等紳商領袖。其中,以葉德來積極投入吉隆坡重建工作的剛毅表現,惟有放置在馬六甲華社近三百年的文化教養與儒家思想的承襲,才能說明其事功與作爲。通過釐清馬來亞境內華社歷史的經驗,或可展現出三百年來逐步形成多元文化場域的南洋華社的研究方法。首先,歷史中南洋域內的華裔,必須放置在其華人聚落中考察。在其華人聚落中,我們需要關注種種公益組織,如廟宇、義山、會館;而在公益組織之中,我們進而考察其具體的運作模式。在其具體的運作模式之中,通過所有能夠掌握的文獻,我們得以考察其關鍵詞的思想意涵;為了釐清思想意涵,我們需要依據儒、釋、道等相關的文獻內涵,加以對證。於是乎,我們從中華文化傳統的思想脈絡中,得以解讀境內的文獻;解開文獻的義涵,則得以看到華社組織運作模式的特殊性,進而把握華社在歷史演進中的生活需求與局限性。
陳威睿博士〈汪克寬對朱熹春秋學思想的闡發〉一文指出,歷來學界對朱熹 (1130-1200)《春秋》學的認識,多主張其對「例」之方法的反動,並循此剖析其「只如看史樣看」的方法所衍生的詮釋困境。然而,在這種認識下的朱熹《春秋》學方法,徒存「據事直書」的泛論,而未能有更深入的探繹,亦難以解釋元、明儒者解經必祖述程、朱的現象。文章中遂據此問題意識開展研究,依照元儒汪克寬 (1301-1372)《資治通鑑綱目考異》、《資治通鑑綱目凡例考異》及《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部著作,探究汪氏對朱熹《春秋》學有「例」的觀點,實出於對「例」的義界不同。再與《公羊傳》、《穀梁傳》的一字褒貶相較,汪氏視朱熹之「正例」為祭祀、災祥、兵事等攸關國家之大事,從禮儀的建制彰顯其義;「變例」則是非為大事之列,卻猶存勸善戒惡功效的事跡,從「為什麼錄存此事」來揭櫫孔子 (B.C 553- B.C 479) 寄存的義理,視「事」為「事類」,去除稱謂例、一字褒貶的介入,成為一種新的「例」體。汪氏認為,朱熹此「例」之義理是上體《春秋》而來,具有絕對的效力,因而透過《綱目》書法的探究,建立朱熹解經之「例」,據此校讎《綱目》,並援胡《傳》之義將綱目書法上繫於《春秋》。如此則胡安國 (1074-1138) 與朱熹之說互惠共通,胡《傳》延續程頤 (1033-1107) 詮釋脈絡,並取得朱熹「例」用此義的證明,強化其說解經的效力。《綱目》則通過胡《傳》所釋義理,追溯其「例」竊取《春秋》大義的根源,揭示朱熹詮釋《春秋》的思想。其中唯一的限制,即是要小心不要使用胡《傳》「變例」來闡釋《綱目》的「正例」。
此文研究之旨歸,是想提供對於朱熹《春秋》學觀念的再思考,排解為什麼《語類》與《文集》會同時出現否定稱謂「例」;卻又說《春秋》有「例」的矛盾,也能說明《綱目》與《春秋》的關係,由此消解朱熹以史視經之說降經為史的可能性,保存通過例來解釋經義的空間。此外,也能解釋元代承繼朱熹志意以撰《春秋》經解的學者,比如吳澄 (1249-1333)、俞皋 (1503-1579)、鄭玉 (1298-1358) 等人,多嘗試通過重新義界「例」的內涵,延伸朱熹解釋經典理念的學者,建構與三《傳》、前人學者定義有別之「例」,其共通的特色則在於去除「一字褒貶」及「稱謂例」的介入。經由以上發現,提供學界探討宋、元《春秋》學的一個新視域。
張力云〈對牟宗三以康德為「居間半途型態」一說之衡定〉一文,旨在對當代重要新儒家學者牟宗三 (1909-1995) 透過援引康德 (1724-1804) 的說法來與儒家,特別是孟子 (B.C 372- B.C 289) 思想作會通,並在相關討論中提出的,認為康德是「處於孟子與朱子之間的一個居間的半途型態」之說,重新衡定及反思。牟宗三基於其圓教的說法,建立在「心與理一」,或者康德所謂的意志能夠成為一「智的直覺」(即「自由意志能真實呈現」的「圓善」)的觀點下,方能達到系統的完成。但從康德對於「人性」的相關說法,卻能夠對牟宗三的說作出反省。本文以此問題意識入手,透過康德對於「人性」與「意志」的相關說法與孟子、朱熹作比較,探討牟宗三所謂「朱子─康德─孟子」型態之說,並對此分判作一衡定。
文中提到,從純理方面,康德強調了「智思界的人性」與「經驗界的人性」的關係是必然兼在的。對康德而言,人之所以為人便是站在這兩重觀點 (two stand points) 下,面對感性欲求以及無條件的道德法則。有別於孟子強調人性是既超越又內在的;而朱子是在肯定超越意義人性之純善(理的純善)的同時,又強調人需要在經驗中去努力實現、使此人性得以彰顯。從此角度來看,孟子與朱子的說法雖然進路不同,但二者對於「人性」的先驗認同感,明顯是高於康德的。在康德的說法下,人的兩重身分不能夠被泯除而需兼具,也因此人永遠都是在努力實踐而永遠答不到的實踐的路上的。這是在比較消極層面來說的人性的實踐,因此,若要正面肯定此價值被實現,在康德的說法下,只能靠是設準的上帝來保證。可以說人性的價值並不能只靠人便實現之,即是說人的主動實踐人性永遠達不到完成處。
至於是否如牟宗三所言,康德的說法是一未成熟的講法,其發展是否真能只規於孟子。從上述的討論可知,康德對於人的意志與神聖意志的距離是不容打破的,人的實踐必定不能夠獨自達到圓滿的地步。故似乎未必能夠如牟宗三所說,因為康德預設意志自律,便認為康德的說法只能最終歸於孟子,此點是還能夠繼續討論。康德的理論在牟宗三看來是不完全的、半途的型態的問題,反而是留給了人在經驗中實踐此道德的餘地。這也正是人應該要努力之處,即透過純淨化自己的意志,使他能夠長期維持直接以法則來要求自己,並給出從內而發的道德行動。這很顯然是一漸教的系統,故將康德與朱子、孟子作比對,也可能所謂的「半途型態」者是朱子,而不是康德。因為朱子對於人性的定義的高度,與孟子是相等同的,其即使朱子認為心與理為二,但最終達到聖人境界所謂「豁然貫通」的全幅朗現時,也是完全靠人自己作到;其理論效力高於康德「從上而來的意志肯定」,也與孟子更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