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呂妙芬教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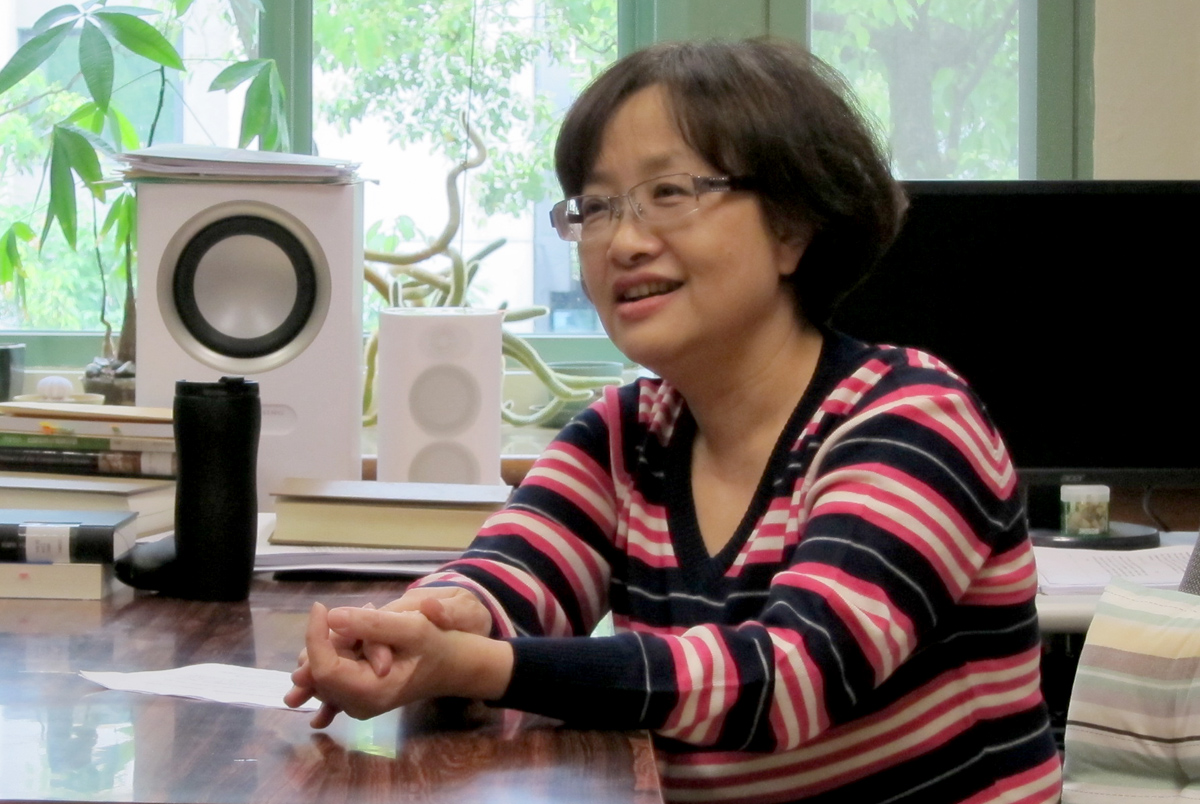
|
呂妙芬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呂教授的專長是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特別是明代理學思想及其相關的社會文化實踐。近年來也關注明清儒學庶民化、宗教化,以及天主教與儒學交涉等議題。已出版學術專書三部,學術論文數十篇。曾榮獲「學術交流基金會奬學金」、「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等獎項。近作《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一書,獲頒 2013 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屆人文及社會學科學術性專書獎」。
走入中文系的天地與投身理學領域
當初會走入中文系的天地,一往無悔地投身理學領域,呂教授說這個選擇和自己年輕時期的生命經驗有關。呂教授大學就讀於清華大學物理系,求學期間參加學校基督徒團契,後來決志成為基督徒。當時參加查經班,《聖經‧舊約》有許多猶太人的歷史文化,心裡總覺對於自己的文化根源知道得很少,即使信仰基督教,也應該多了解自身文化,多讀一些中國經典。呂教授說她和父母商量,大學畢業後想用一點時間去旁聽中文系的課,同時思索未來的路。即將畢業前的某一天,呂教授回憶她走在清華校園,一個想法忽然躍上心頭:何不畢業後去參加臺大中文系的插班考試?當下只單純地希望正式在中文系的環境中學習,如今回首再看當初的決定,呂教授說:「這個插班考試真是影響我一生,我能考進去也很幸運。」就這樣,已經取得物理系學位的呂教授,在同一年九月又進了臺大中文系。從大二唸起直到碩士畢業,在臺大度過了六年充實愉快的時光。
呂教授說自己在中文系那些年,從來沒有想過日後會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只是純粹喜歡在課堂上聆聽教授講課,她說:「中文系每一堂課都非常精彩,詩選、詞選、小說,都讓人樂在其中,任由那些老師引導我進入文學優美的境界。」又說:「重視古典是臺大中文系的傳統,至今沒有太大的改變。我當時都修了許多先秦的課,覺得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光是先秦典籍就讀不完。臺大中文系有一種底蘊,能為學生厚植學術根柢,滋養學生對整個中國文化的情感。」
呂教授說自己到決定碩士論文領域時,想法還是很單純,覺得自己應該多學習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核心價值。她知道理學是宋代以下影響文化深遠的價值觀念,而且長久主導科舉,所以選擇挑戰這個領域,不過當時自己對這個領域可以說幾乎完全無知。呂教授回憶碩一初讀理學文本時,覺得原典抽象難讀,二手著作也不易理解,不但無法解答心中疑難,甚至連要問什麼問題都不知道。然而理學自有一股吸引力,呂教授說她從理學家傳記可以看到許多理學家的生命都經過一個重大抉擇,很多人雖然從小研讀儒家經典,但是到了更晚才真正確立以儒家聖賢之學作為自我安身立命的價值所在。呂教授說:「我彷彿從這些人身上看到和自己生命信仰歷程相近的經驗,總覺得理學的某些價值和我的信仰很接近,後來自己做研究時也常會從宗教信仰的角度去想問題。」因為這樣,就決定以明代理學做為碩士論文的領域。呂教授說當初選擇研究明代理學是很天真理想的想法,幾乎沒有考慮未來出路的問題,而且自己修宋明理學課的成績並不夠好。不過她也慶幸當時可以如此單純,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相信上帝會引領前面的道路。
到現在,呂教授仍相信很多學者會從事宋明理學研究並非偶然,而是有某種思想和生命特質上的關聯。她還記得第一次和碩士班的指導恩師古清美教授見面的情形:「古老師就問我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做這麼枯燥的題目?做《紅樓夢》不是更有趣?我大概跟她描述我上述的想法。她聽完後,笑一笑,就決定收我了。」呂教授接著說:「後來我知道這應該也是她自己的感覺吧!她一直到去世之前都還跟我說,她自己當初如何放棄《紅樓夢》研究,認真用生命去做理學這一塊。她最後一次進醫院,告訴我最遺憾的是:自己在病痛中獲得了更深的生命體會,很想有機會和學生分享,卻再沒機會替臺大學生上一堂宋明理學。」
呂教授的碩士論文是《胡居仁與陳獻章》。她告訴我們當年同學們如何苦惱找碩論題目,自己摸索了好久,想到可以比較胡居仁和陳獻章,因為兩人是同門,但思想差異頗大,前者被視為朱學的殿軍,後者則是心學的開創者,而且兩人又都獲入祀孔廟,學術地位相當且重要。她的論文就透過比較胡居仁與陳獻章,以及朱熹與王陽明,探討由程朱理學到陽明心學的思想史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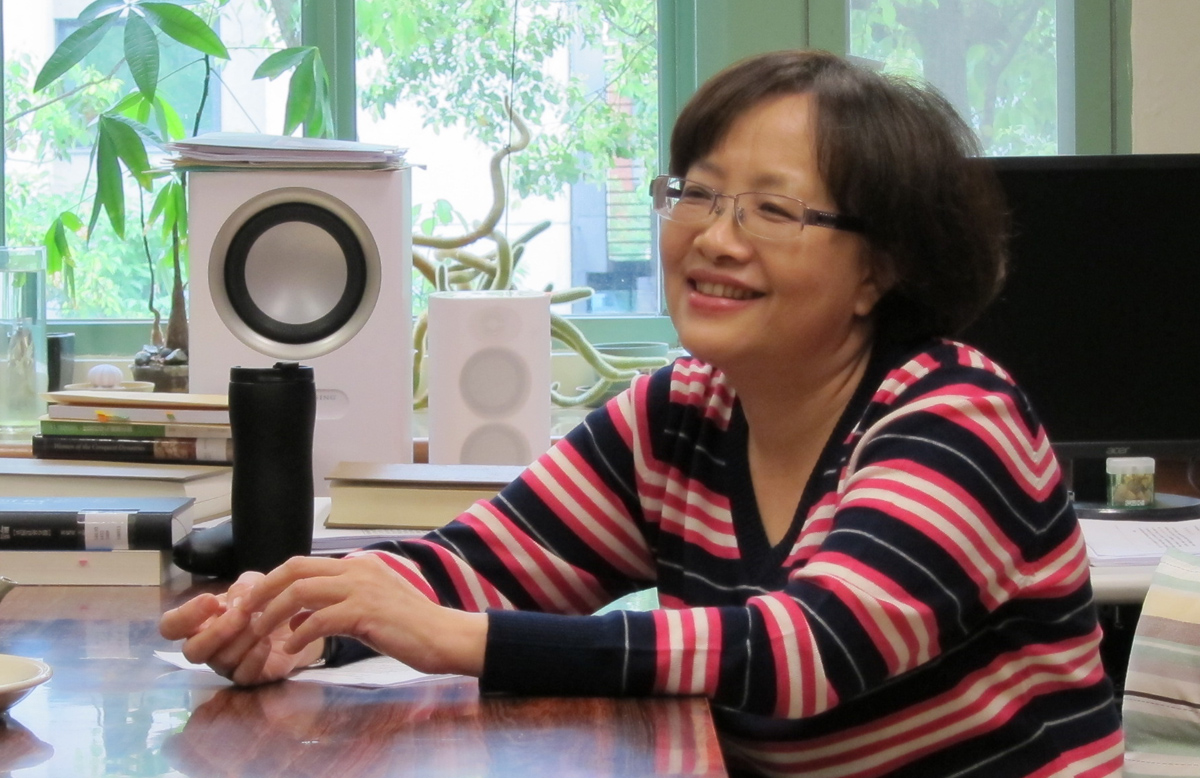
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歷史系求學的甘苦與收穫
臺大中文所碩士畢業後,呂教授赴美求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她說:「我 1989 年碩士班畢業,當時我先生申請到教育部公費獎學金,1990 年到美國 UC Davis 做博士後研究。我在美國當家庭主婦,一面準備考試申請學校,1992 年進入 UCLA 歷史系,師從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教授。」
美國那幾年的訓練讓呂教授經歷了一段刻骨銘心的過程。她說:「如果從前在臺大是悠遊於老師給予的文學饗宴,學生坐在臺下是一種享受;那麼我在美國所上的課程,我必須說都是苦學、困學,主要是因為訓練不一樣。尤其修課那三年,真的很痛苦。」痛苦來自於學術思想的訓練過程及方式與過去迥異:「我初到 UCLA 歷史系的時候,艾爾曼教授上課的方式基本上全部是英文的二手研究,他要引導我們進入一個議題或領域最新的研究狀況,這些議題我都不熟。這和我在中文系的訓練很不一樣,當年我們在中文系大多是熟讀某部原典,然後在原典裡面找問題。我所熟悉的古文,在 UCLA 用不到,英文也不夠好,對新的領域與訓練方法更不熟悉。當時已經博士班一年級的我,從來沒翻過方志。」
她回想起當時修課唸書時,緊張之情仍記憶猶新:「課前就要讀完一本英文書,如果修兩門課,就要讀兩本英文書。艾爾曼教授每次上課前要先交報告。讀三百頁的英文書對我來說很痛苦,寫報告又寫不出來,第一年的生活除了吃飯、睡覺、洗衣、買菜,其餘時間都坐在書桌前讀書。竭盡所能,仍然做不好,一輩子從來沒有那麼挫折過!而且不知道能不能畢業。我覺得始終達不到老師對我的要求,一開始連同學在討論什麼我都聽不太懂。課程再多、再好,修二、三門已經是我的極限。」
呂教授說現在覺得那樣辛苦的訓練是很寶貴的經驗,雖然幾乎壓過自己能力和心靈的底限,「可是我很慶幸自己沒有放棄,我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想法:正因為我有不足,所以才需要學習;不是因為自己很優秀,要來展現。」接受了歷史系的訓練,呂教授說自己體會到對歷史學門來說,時間軸非常重要,不同於以前在中文系時習慣用天馬行空的方式來想像文本的意義。她說:「雖然我沒有上什麼歷史方法學,可是自己讀到後來覺得最重要就是兩個軸:一個是歷時性的變化,一個是同時性的社會結構關係。我是從別人的作品和課堂討論,才非常有意識的把時間軸放在心裡,思想文本中的某句話在什麼情境下被訴說,反映怎樣的社會脈絡,同一本書在不同時期被重刊的意義,或者後人對前人和前代歷史的建構等問題,這些都離不開對於時間軸和社會的思考。」
艾爾曼教授對呂教授的啟發特別多,他會逼問學生,讓學生去想一些問題。呂教授說:「艾爾曼教授收我當學生,大概很想改造我,他告訴我不能用寫碩論的方式寫博士論文。他常會問我思想、人物、學派外緣的問題,例如某個理學家出生什麼樣的家庭?何時考上進士?他的經濟來源是什麼?他的政治關懷是什麼?有沒有隸屬於哪個黨派?他的朋友是誰?敵人是誰?跟僧侶或商人的關係如何?他還問我怎麼知道王陽明真的在龍場有悟道?他讓我必須認真去想許多問題,提醒我觀念和觀念之間不是自然就會相互影響,還得要有媒介、機緣才有可能。」
呂教授說艾爾曼教授曾告訴她,研究明代陽明學大概就是 150 年的歷史,只要跟那個時期有關的政治、社會各方面,都應該要了解。艾爾曼教授還說:「你的論文要像一扇窗戶,讓你的讀者透過你的論文,可以看到明代的政治和社會等其他問題,而不是只有王陽明的思想。」呂教授說雖然自己覺得這個要求很困難,但終身受用。呂教授說 UCLA 其他老師的課也都很精彩,例如她上了萬志英 (Richard Van Glahn) 教授的晚明史,就是用年鑑學派的總體史的概念來開課,每一週討論一個大主題,從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學術思想、文學各方面談研讀晚明史。這些課程讓呂教授覺得眼界大開。
在美國除了良師,還有益友相伴。呂教授說:「我也很感謝我 UCLA 的同學,楊瑞松、廖咸惠、祝平一等人,我們很熟,彼此之間有很多的討論。」她說回想起來仍深深覺得能夠在那個時代的 UCLA 歷史系學習實在非常幸運,當時中國史的老師大概只有四十幾到五十幾歲,充滿研究活力,在美國學界都是一線的學者。她說:「我們同學都會說,我們擁有美國漢學界第一流的老師,但我們自己是二流的學生。那是我們真正的感覺,覺得自己還不夠好,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時間很有限。」
對臺灣高等教育培育的反思
在臺灣與國外都接受良好教育的呂教授,比較兩國培育高等人才(特別是博士生)最大的差異,她認為兩國各自培育的重心不同,各有優點,但美國對於菁英的培育所投注的金錢是遠高於臺灣的。呂教授說:「我看著我那些在美國修博士的美國籍同學,他們申請到的獎學金很多,可以用獎學金到中國、臺灣、日本學習語言或蒐集資料,而且時間可能長達2~3年,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獎學金的來源不僅是政府,很多由民間基金會提供,為學生造就良好的機會。」
回國後看到臺灣博士生的情況,令呂教授感觸良深。呂教授說許多人文學的博士生為了賺取學費、生活費,最精華的時間多用來教書或打工,沒有時間好好作研究、寫論文。因此臺灣博士生的修業時間很長,但寫出來的論文却未必很好。美國學者往往會積極將自己的博士論文修改後出版,成為自己第一本重要學術專書,這方面我們還有進步的空間。不過,她也說近年來已經看到一些臺灣博士論文在畢業後兩三年內修改成優良的專書出版,這種情況有越來越多的趨勢,這是值得肯定的。
整體而言,呂教授認為,臺灣如果在制度上可以提供博士生比較高額的獎學金機會,讓他們無生活後顧之憂,得以專心唸書,然後對課程的要求再嚴格一點,多給一些壓力,相信對本地博士的培育會有正面的幫助。
思想與實踐之間:陽明學講會的研究
《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是呂教授據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首部代表作,榮獲 2003 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本書以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取徑,探討有明一代陽明學的興衰。除了循時序描述陽明學派的建構、後續發展和地方講會的歷史外,同時也關注學者個人思想內涵、議題論辯、學派內部差異、學者個人乃至群體的行動及其政治意涵,以及明代教育與科舉制度所衍生的社會現象,例如士人群體在社會結構上的變化等。其中,「講會」此一陽明學賴以傳播的社會組織,在性質與實際運作上關涉著明代士人群體乃至地方社會中的政治與文化,為本書核心所在。
呂教授以陽明學講會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重心之前,從論文題目的選定,到確立問題意識、議題興趣、研究方法,都不斷徘徊於中文學門與歷史學門的訓練之間。她說當時修習的課程對她有很深的影響,她選擇研究明代理學是忠於自己的興趣,雖然艾爾曼教授自己是研究清代學術思想為主,並不是明代理學。呂教授用一個例子說明自己在 UCLA 接受教導後的變化,她說以前在臺大也讀過《王龍溪語錄》,但只注意書中對「良知」的許多討論,但到了博二時她再讀同一部書時,就會為了想知道王畿和誰通信,因而看到許多講會的紀錄。她說:「以前我只留意他們討論良知、心性問題,幾乎對『講會』的史料視而不見;但當我開始注意他們參與講會活動時,那些材料就鮮明起來,而且相當豐富。」彷彿回到那困頓之後豁然開朗的時刻,呂教授眼裡閃著亮光,語氣興奮地說:「當我找到講會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覺得它比較具體,符合我在歷史系的訓練。一群活生生的人聚集在地方上,不管他們思想上是否有突破,我都可以面對社會史家說,這是發生在晚明地方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而且這些講會史料可以讓我把理學家思想內涵和他們的行動(實踐)結合起來研究。」
呂教授又說:「以前的學者談講會是將它置於書院史脈絡,可是我在讀材料時,發現講會不是書院史的一部分,講會是人的聚集。」而「人的聚集」這個概念也帶給呂教授很多的聯想,她想到當前各種團體、學生、婦女或上班族舉辦的讀書會,或是在咖啡屋、教會、家中聚會,一群人可以藉著讀書聊出各種偉大的志向,也可能匯聚成改變社會的行動力。人的聚集具有創造力與能動性,可以超越一個地域、建築或有形的框限。呂教授認為,陽明學的講會具有創新的能量,同時又與當時政治、社會、經濟條件相關。
呂教授陽明學講會研究的緣起一如上述,從1993年構思題目,1995年考過論文大綱,1997 年完成博士論文。一路走來,既有內心徬徨不安的時刻,也有遊移於中文與歷史研究方法的糾結過程。然而正是這樣的經歷鍛鍊了她的研究,成功地琢磨出一條視野宏闊的道路。

呂教授辦公室窗戶,呂教授說她特別喜歡這扇窗,進研究院工作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面對這扇窗完成的
近著《孝治天下》:會通經典文本與近世思想文化史的典範之作
呂教授的近著《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文化》,問世以來,佳評如潮,2013 年 10 月榮獲「中央研究院第三屆人文及社會學科學術性專書獎」。此書透過《孝經》此一特定主題,討論從晚明到民初《孝經》學與相關文化實踐。一、二章為長期社會史和學術史背景,三至五章探討晚明的《孝經》論述與實踐,六至九章則依時序討論從清初到民初的變化。整部著作從政治、社會、思想、宗教、經典詮釋、性別、儀式實踐等角度深入考察,呈現《孝經》與人們生活及思想交會的豐富景象。此書可以說成功會通了經學史、理學史、政治社會與思想文化史,既能深入文本的分析,更能結合寬廣的視野,是呂教授繼《陽明學士人社群》之後又一部重要著作。
呂教授與我們分享了當初走入《孝經》研究的機緣,她說曾偶然在日本陽明學者中江藤樹的書中看到一篇觀想《孝經》的文字,文中記載著某種儀式和觀想的活動,又和《孝經》有關。她知道日本的陽明學者很重視《孝經》,但是當時她只是想自己研究陽明學這麼久,從來沒有把陽明學跟《孝經》聯繫在一起,也想知道晚明中國是不是也有類似和《孝經》有關的觀想實踐。後來她從楊起元的著作再次遇見〈誦孝經觀〉這篇文字,才決定撰寫這個議題的文章。開始的時候因為找了明代刊刻的《孝經》本子來讀,很快就發現內容豐富,遠超過當初自己的設想,這樣就開始了一個新的研究。
呂教授說她最初只想從不同角度去寫晚明的《孝經》,但是做到蒙學時遇到很大的困難,花了許多時間才完成那一章的研究。又因為體會到清代對此議題的重要性,幾乎在研究進行三年之後,終於鼓起勇氣走出晚明,跨入清代。呂教授說:「走入清代對自己是一個大膽的挑戰,幾乎找不到研究的下限,愈往下做,好像需要跨越的心理門檻愈高,因為太多東西都不夠熟悉,也因此這本書才會寫這麼久。」
在《孝治天下》中,隨處可以看到本書蒐羅資料的全面,諸如龐大的文集、方志、二十四史、各朝會要、善書、長時段的各種主題的二手研究等,盡在其掌握之中。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一本重要著作背後,是孜孜矻矻、無比紮實的史料耕耘過程。
主持「近世儒學、家族與宗教工作坊」的理念
呂教授在研究院繁忙的行政事務之外,也主持「近世儒學、家族與宗教工作坊」讀書會,對後輩的引導、提攜不遺餘力。工作坊的主要成員為各校中文系、歷史系的年輕教授、博士後研究員,以及博士生。呂教授謙虛地說:「這樣的活動不是我帶領大家,它是一個討論與交流的機會,我自己從中學到很多。」
成立這個工作坊源於兩個很實際的想法。首先,呂教授曾經分別受過中文與歷史學的方法訓練,學成之後便自然而然注意到中文系與歷史系學生缺乏交流。兩系都有人研究明代或清代學術思想史,但卻互不相識,她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事;如果彼此多一點接觸,應該能夠彼此學習。呂教授懇切地與我們分享她的親身經歷:「我從中文系到歷史系,不是受到很多的啓發嗎?連問問題的方式都不一樣。歷史系學生問問題的方式可以為中文系學生打開另一片視野;同樣的,中文系學生閱讀文本、發掘文本問題的能力與功力,也能為歷史系學生帶來一些啟發與幫助。」
呂教授經營工作坊的第二個理念,是希望同領域的學人之間能夠聚在一起,群策群力,共同研討。透過討論可以得到很多收穫,這來自她過往在美國求學時的感悟:「我記得在美國的課堂上,學生的專業領域差異很大,但都可以討論,也許因為環境就是這樣,中國史的學生不多,如果一定要找到和自己研究同一領域的人才能討論,那就很孤單。我想只要願意交流,任何議題的文章,我們都可以從對方想問題的方式學到東西。」不但不同領域的學人可以相互切磋,若是能集結明清學術思想史的同好,彼此幫助提昇,這樣的力量更不容小覷。呂教授有感而發地說:「尤其當我們寫了一篇文章要發表、投稿之前,如果能有讀書會的朋友一起幫忙看過,提供修改的意見,這樣的論文品質會更好。」
呂教授說學術研究不能閉門造車,她特別重視一群同好能常常聚在一起討論學問,形成一個友好的學術社群,這不僅是學術紮根的工作,也是人生難得的情誼。基於這樣的理念,她希望工作坊能夠持續運作下去。

對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的期許
現在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已正式隸屬於中央研究院,由院方撥予經費,四個研究所合作,共同推動明清研究。身為委員會的一員,呂教授對未來發展方向寄予厚望。她說:「我很希望它不是少數人的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而是一個創造學術交流的平台,可以聯結起明清跨領域學術研究的管道,讓院內更多明清研究的學者都能利用這個管道舉辦學術活動和讀書會。也讓中研院的學者也有機會接觸國內各大學的教授和研究生。如果這個委員會可以讓很多人都覺得它與自己有關,我們就成功一半了。」呂教授也說「第二屆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公開徵稿的方式籌辦,各方參與相當踴躍,獲得熱烈的迴響,令委員們都感到欣慰。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未來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