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安教授演講「天吏:明清科舉考官的閱卷工作」紀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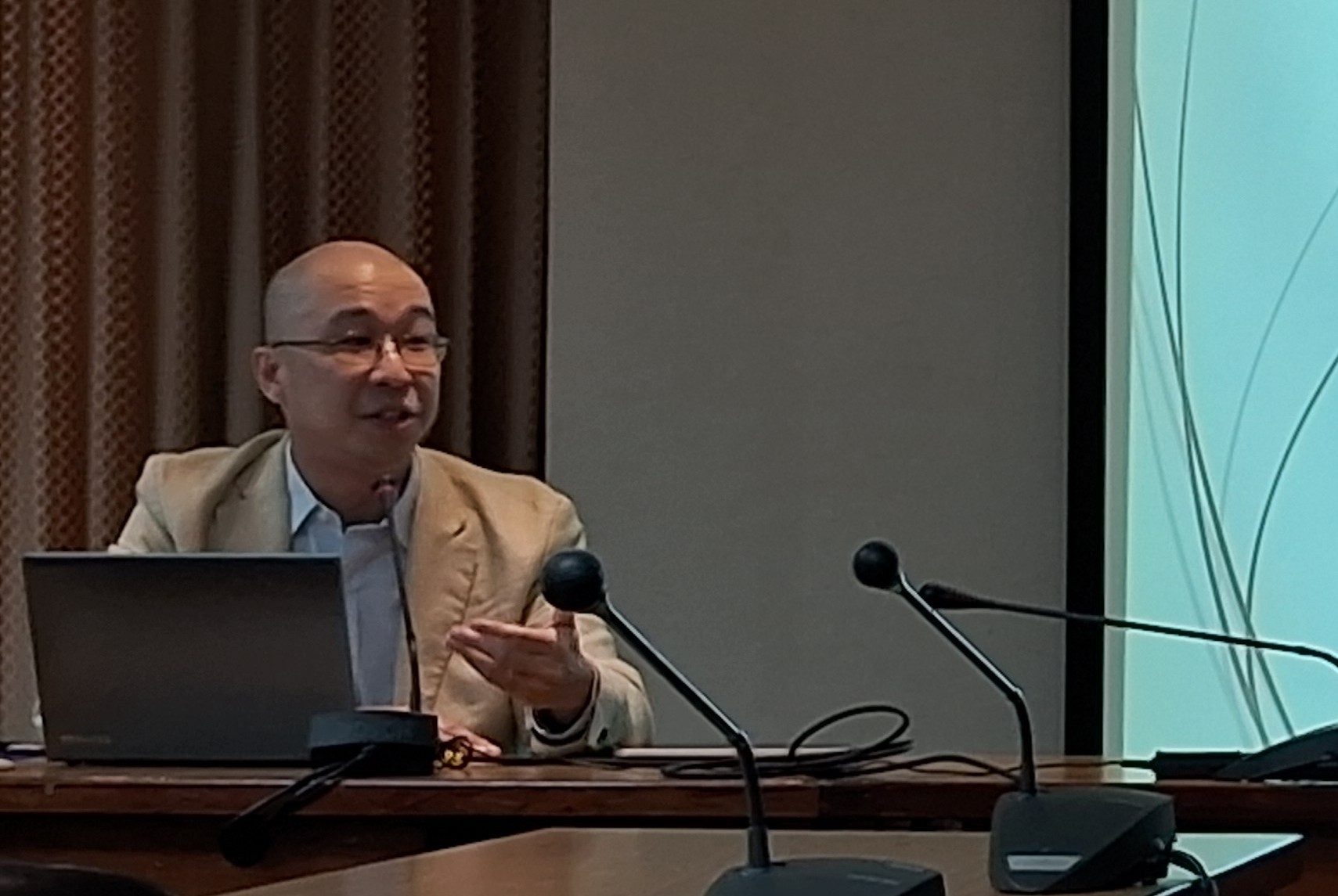
|
本次演講,是中研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上升的階梯──清代士人的科考生活」展覽 (2024.10.19-2025.04.16) 系列演講的第三場。主講人徐兆安教授,近年潛心研究明清至近現代的考試制度,不僅進行了許多細緻的考證,更將討論擴及政治、社會、文化等各種層面。就徐教授看來,科舉研究發展至今,儘管已經累積了豐富的成果,但仍有許多細節尚未獲得釐清。其中一個原因,是相關材料太多、條文太詳,讓人往往誤以為原文意義已經顯豁,不再進一步掌握其中各種複雜的術語。本次演講的主標題「天吏」,是晚明士人顧大韶 (1576-?) 將「盲考官」與「庸醫」、「低風水」(不會看風水的風水師)並論所給予的諷刺性稱號。徐教授認為,科舉考官之「盲」,實可透過制度下的種種細節進行探討,比起考官個人的無能或失德,其更可能源自這套看似嚴密的複雜系統,在運作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盲點」。
徐教授首先介紹明清鄉、會試閱卷的各個環節。相關作業在分工上可劃為外簾與內簾,外簾人員負責收卷、彌封、謄錄等程序,將收上來的考生原卷(墨卷)蓋住姓名,並以紅筆另抄為硃卷,送至內簾,先由各考房的同考官(或稱「房考官」)進行一輪批改,再由主考官審閱篩選過後的卷子,決定中取者。批閱硃卷時,同考官是使用藍筆,主考官則使用和考生同樣的墨筆。墨筆有改動原卷的可能,在內外簾都是被管制使用的工具,因此只有主考用墨筆,象徵其權威。最後則根據結果,拆下錄取考生原卷的彌封,將底下的姓名填上榜單。為了減少流程中的錯誤與弊端,明清科舉亦設有由專員檢查批改後試卷的「磨勘」程序。放榜之後,落第考生還可領回自己的試卷,由上頭的批語和圈點瞭解考官的看法。
無論是將成千上萬名士子聚於一地,進行長達數日的考試,還是考官必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批閱成千上萬份由十幾篇文章組成的卷子,都不難想像實際運作過程中,可能出現各式各樣的問題。而科舉制度從明到清的一些變化,又為原本運作就已相當龐雜的流程,帶來更多混亂的因子。相較於明代,清代批閱機制有不少地方都反映出對同考官的不信任。明代主考官通常不會推翻同考官的篩選結果,而清代主考官卻可透過「搜落卷」,從已被同考官淘汰的試卷中,另行挑選欲錄取者。原本科舉分房的設計,除了明代時以考生所專之經進行劃分──這點隨著乾隆晚期改為五經並試而失去意義──也有避免考官接觸所有試卷,以減少舞弊空間的用意。但「搜落卷」於清代受到鼓勵,便使得圍繞主考官所進行的「通關節」手段,以及主考官依據特定學說選才的作法成為可能。徐教授還提到,現有的研究其實低估了「搜落卷」的影響力,預設考官會為了避免在後續的磨勘階段擔責任,而儘量避免此類易引發爭議的行為,但其實在制度壓力下,同考官通常會選擇讓步,主考官也能透過事後「補用薦條」等非正規的手段,消除自己推翻同考官推薦的痕跡。
此外,清代考官推薦試卷的程序,也與明代不同。明代同考官批閱自己負責的考房試卷,篩選中意者向上推薦,不需聯名他人,結果亦不會被推翻,故對考生的影響力更勝主考官。而清代則將同考舉薦從一人改成五人同薦,主考官取卷也規定要四人聯名共薦,等於攤分了他們的影響力,從而削弱了考生與考官關係的緊密性。
彌封、謄錄、批閱、拆封、填榜,要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限內,完成所有試卷的處理流程,本就過於倉促,而清代自康熙五十年 (1771) 起,甚至僅將出榜之期「多展數日」,就要求主考官必須「盡閱卷子」,更是強人所難。由於試卷遺失、損毀、未被上呈而無法中取,成為明清善書論述因果報應的常見題材,抑或士人久第不中的自我辯解,雖不見得皆為事實,卻頗能反映試卷處理過程中各種「黑數」存在的可能性。為趕在時限內「閱」完大量的考卷,亦產生了諸如「首場考試決定勝負」、「房考舉薦先到先得」等現象。這意味著每一次科舉考試,其實都有許多考卷沒有被好好看過。明末艾南英 (1583-1646) 將自己的會試落卷──首篇文章只被點讀了四行──刊刻出版,以示抗議,引發了極大的轟動。後來便規定考官形式上必須將試卷都圈點過一遍,並為清代所沿襲,進而無可避免地衍生出交由他人代點的情況。有限的工作時間、數量龐大的試卷、繁雜的作業程序,由上述種種因素導致的混亂,最終仍可透過這樣的「後製」手段,產出看起來井然有序、似可令人信服的書面結果。
明清科舉中所稱的「硃卷」有兩種,一種是以硃筆謄錄的批改用卷,另一種則是考生中取後刊刻自己的答卷,送給親朋好友的版本。徐教授認為,將上述二者的現存實物相互比對,或是對照官方後續透過會試錄公布的內容,或許都能發現不少修改、加工的痕跡。例如中試者自行刊印的硃卷內,能看到篇幅頗長的同考官評語,四位主考也都各留有一句評語,但現存的實批硃卷上,則沒有同考評語,四位主考亦只共有一句聯名的評語而已。如果研究者根據刊出的硃卷,認為其所錄評語確實能代表各考官彼時的立場,就可能產生很多誤解。
磨勘這個程序,最遲在晚明就已存在,但目前留下的成文材料多是清代的。主要是將鄉、會試的考卷(包括硃卷和墨卷)送至禮部,由臨時組織的專員團隊進行檢查。查核對象涵蓋考生、外簾人員和考官。考生違規方面以避諱、抬頭等格式錯誤為最大宗,這些格式的規定繁瑣,標準甚至可能一直在變,卻足以能讓原本中取的試卷落選。針對外簾的檢查,主要留意謄錄程序有否出錯、有否改動墨卷;針對考官的檢查,則在於是否按程序圈點、薦卷和取中。當時還由此發展出一種「生意」,如清末長沙縣衙就有擅長「洗改」的書吏,可以在試卷送勘前,不留痕跡地幫考生改掉當中的格式錯誤,藉此收取報酬。
在演講的最後,徐教授強調,宏觀的歷史討論固然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微觀的歷史考察亦有其重要性。特別是目前學界於歷史的微觀面向理解不多,但很多時候那些最細微的層面,卻對歷史、人事的根本性理解至關重要。而要對歷史細節有臨場的認識,就必須知道相關制度實際上是如何運行、過程中會產生哪些狀況。此類細節很多均未留下條文或記載,只能依靠周邊的材料來研究。徐教授更指出,科舉研究至今仍在持續進展中,尚有許多深掘的空間,而其實際運作過程中衍生的諸多混亂與問題,能於歷史解釋上提供的啟示,就是研究者應走出功能論與動機論的視角。過去討論科舉,大多注意該制度如何造就社會流動,但從社會流動的視角出發,將無可避免地聚焦在少數的中式者身上,而忽略絕大多數落第的參與者。再者,社會流動是科舉帶來的效應,不應該取代對於制度本身的探討。參與或影響此制度的各類行動者,懷揣不同動機,彼此衝突、相互抵消,也讓科舉不能以單一功能或動機來衡量。換言之,若將歷史想像得太宏觀、太整齊,或許反而可能阻礙研究者理解當中的人情世故。
徐教授復將鄧小南先生「活的制度史」,以及書籍史的概念帶入討論,認為前者具體方法在於探究「行政」或「手續」的歷史,後者則頗關注書籍之形式及物理形態對其內容的影響,這些思維其實都可以納入明清科舉的研究。好比「文書旅行」雖是一個批評官僚主義的諷刺性詞彙,卻能無比貼合試卷在科舉流程中輾轉遞送、處理的過程。而這段經由實際制度運作開展的「文書旅行」之歷史,亦是呈現許多體制變遷與人情世故的重要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