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教授演講「當『亞細亞』遇見『九州』:重思利瑪竇與衛匡國的中西地圖交流」紀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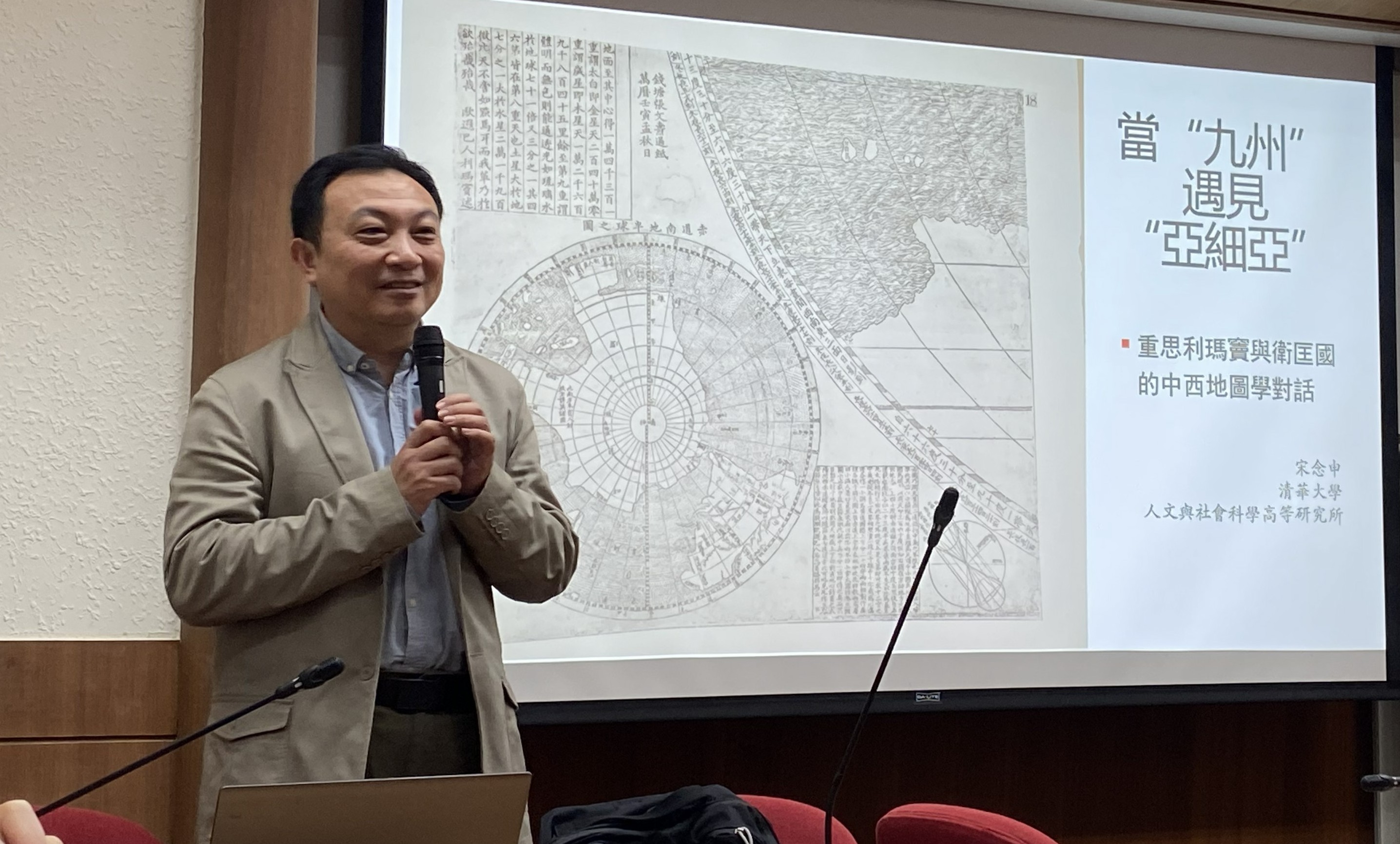
|
在本次演講中,宋教授以傳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與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為切入對象,從東、西地圖學或地理學知識「相遇」的角度,探討九州和「五大洲」兩種大地的想像,是如何形塑亞洲這一概念。
先從利瑪竇談起,1602 年應萬曆皇帝 (1563-1620) 的要求,利瑪竇在李之藻 (1571-1630) 等中國學者協助下,在北京刻印《坤輿萬國全圖》,這幅地圖也是利瑪竇所製地圖之中,最大的世界地圖。對利瑪竇而言,在中國繪製地圖不僅是地理知識的交流,更是傳教方式的一環。正因為利瑪竇想傳教的動機,產生兩種文化的碰撞與轉譯,促成宋教授能以此分析利瑪竇是選擇何種概念詮釋「亞洲」,並使之得以進入中國。
不過,在進入談論 16、17 世紀東西地圖學交流史之前,宋教授先回過頭來講述東、西兩方各自的地圖學概念。關於歐洲知識傳統中的大地觀,歐洲人很早就猜測大地為球形,從中世紀流行的 TO 地圖來看,所有陸地被 T 字型的河流或海洋分為歐羅巴(左下)、亞細亞(上方)、利比亞(亞非利加)(右下)三大洲,外圍有 O 字型的海洋包圍。此時歐洲人認為球面上是所謂的人居世界 (Ecumene),這個詞彙源於希臘語 οἰκουμένη γῆ。宋教授補充,這概念很類似中國古代的「天下」。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因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aeus, 100–170)《地理學指南》,在歐洲的翻譯與印刷而受人重新認識。歐洲人繼承了托勒密繪製地圖的方式,成為日後現代地圖的原型,比如運用數學計算經緯線。此外,書中記載的地理概念,也刺激大航海時代的興起。
與歐洲不同,以中原為核心的東亞地區地理觀,一開始便有著天圓地方的觀念。而從中國地理學發展來看,彼時地理概念能追溯至《尚書.禹貢》中的「九州」,典型案例便是 12 世紀以「計里畫方」的方式,繪製精確度高且以網格製圖的《禹跡圖》。而在「九州」空間之外,則是名為《華夷圖》的地圖。《華夷圖》雖然涵蓋更大的世界,但並未等比例的繪製,其中原以外的地理知識,往往只用文字描述呈現。朝鮮王朝初期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02),是當時東亞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地圖,從對於南亞、非洲的描繪來看,可能吸收來自阿拉伯商人的地理知識,但其地圖主體區塊仍然有《華夷圖》的影子。
16 世紀隨著大航海、印刷術流傳,以及地圖商品化,許多製圖家族互相競爭地圖市場,從而發展出以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為中心的尼德蘭製圖學派。其中具代表性的地圖是,1570 年由亞伯拉罕.奥特柳斯 (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出版的地圖集《寰宇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其中的世界總圖繪製了南、北美洲,海岸輪廓粗略的東亞,以及想像中的南方大陸;而此圖是後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最重要母本之一。1584 年版的《寰宇大觀》中,也加入了一張《中國圖》。該圖的主要內容依據《馬可.波羅遊記》的紀載,這是歐洲最早以中國命名的單幅地圖,並且主宰歐洲的中國地理想像近一百年。也就是在這一年,利瑪竇在肇慶繪製首張以歐洲地圖為母本的中文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圖》。此後利瑪竇又應邀,繪製了多幅世界地圖。到了他繪製《坤輿萬國全圖》時,利瑪竇除了參考奥特柳斯的地圖之外,也參照羅洪先 (1504-1564) 所繪製的《廣輿圖》。關於利瑪竇如何向中國人解釋歐洲的地理概念一事,可以在《坤輿萬國全圖》的序言中找到。
首先是如何讓「地球說」與「天圓地方」觀念相容?在《全圖》序言中,利瑪竇借用「渾天說」的術語,認為「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黄在青內」——此語不但明確表達地球說,並且借用張衡 (78-139)「渾天說」中的雞蛋比喻,弱化新說的異質性。利瑪竇還重新解釋所謂「天圓地方」,強調「方」不是說大地的形狀,而是說明其「定而不移」的性質。接著,利瑪竇向中國人講述「大洲」的概念,說地分成五大「州」:歐羅巴、利未亞、亞細亞、南北亞墨利加、墨瓦蠟泥加(未知的南方大陸)——在這裡借用了「九州」的「州」字。值得注意的是,這幅漢語地圖首次將「華夷」概念置換成「萬國」的概念,暗示中國只是萬國中之一國。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利瑪竇的時代,歐洲文獻提及「人居世界」的組成部分,往往直呼其名(如 Asia 亞細亞),不然就是用「部分」(part)。彼時歐洲語言中的 continent 一詞,尚未固定用來指稱今天的「大洲」。以 18 世紀為例,continent 所指的地域可大可小,有時指稱大陸,有時指大的島嶼。而利瑪竇創造性的運用九州語彙中的「州」概念,來解釋「人居世界」的大地結構。換言之,利用一個抽象的概念洲(或州)統稱地球的大陸板塊,實際上在漢文先出现,早於歐洲語言。另一個佐證是,日語與朝鮮語種的「亞洲」(アジア、아시아),就是直接音譯 Asia 一詞,而並沒有「州、洲」這樣一個詞意單元。
在利瑪竇之後,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 1649) 在利瑪竇與龐迪我 (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 等耶穌會士的遺稿上,添加新材料,並於 1623 年出版了近代首部介紹世界地理的中文著作《職方外紀》。其中〈亞細亞總說〉提到:「亞細亞者,天下一大州也。人類肇生之地,聖賢首出之鄉」,再一次以「州」稱呼人居世界的不同部分。宋教授補充道,這段聖賢首出之鄉,中國讀者可以認為「聖賢」是指孔孟,而在歐洲人特別是傳教士那裡,也可以是指耶穌,這段敘述保持雙方都能解釋的模糊空間。同樣是在弱化不同文化的異質性。
本演講的第二位主角,衛匡國。生於義大利,1631 年加入耶稣會,1642 年抵達澳門,1643 年居住在浙江杭州。翌年,明清鼎革之際,親歷其中的衛匡國留下了記載滿洲征服的第一手資料《韃靼戰紀》,並選擇投效清朝。之後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派遣衛匡國回到羅馬,爭取教廷對於中國禮儀的栽定,此舉暫時緩解禮儀之爭的問題。1655 年,衛匡國《中國新圖志》(Novus Atlas Sinensis)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並成為荷蘭製圖世家瓊.布勞 (Joan Blaeu, 1596-1673)《大地圖集》(Atlas Maior)之一卷。與早期地圖相比,衛匡國的地圖集是歐洲第一部中國分省地圖集,其中還包含日本列島、蝦夷地、朝鮮半島等地理資訊。在中國總圖中,衛匡國以「帝國」(Imperii Sinarum) 來定義中國,而非過去歐洲地圖中常用的王國 (kingdom)。衛匡國的地圖,是以《廣輿記》為底本,再予以加工。《廣輿記》中的地圖底本,也是羅洪先的《廣輿圖》。衛匡國的貢獻在於,他運用數學方法,將本以計里畫方為方法的《廣輿圖》,重新畫上經緯度網格。此做法讓中、西地圖學知識融為一體。
宋教授指出,利瑪竇與衛匡國的遺產,代表著早期全球化的一個側面,二人所繪製的地圖,各自面向中國與歐洲的讀者,並且在東、西各自的傳統中,都是開創性的新作品,同時也結合東、西的地圖學知識。它們既是歐洲的,也是中國的;這種文化融合的情況,是典型的全球化現象。誠然,不可否認在早期全球化之前,各地文化就已經在不斷交流、融合。但歐亞大陸兩端的系統性交往,是從 16、17 世紀,借由西歐和東亞各自現代性的開端,才有其實現的條件。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也傳播到日本與朝鲜,並深刻影響整個東亞的地圖學。日本方面,諸如僧人浪華子(本名鳳潭,1654-1728)所繪製之《南瞻部洲萬國掌菓之圖》(1710),地圖左上方,畫出多個歐洲國家,如英國和荷蘭,但地理形狀是虚構的。此外還有以「南蠻地圖」為底圖,製作的《世界及日本地圖屏風》等一系列地圖屏風;或是長久保赤水 (1717-1801)《地球萬國山海輿地全圖說》(1780)。朝鮮方面,如《輿地圖》(約 19 世紀),從中可見,朝鮮人對於利瑪竇知識有一些誤讀或傳抄錯誤。不過,這本身也說明,利瑪竇的地理知識,已通過重重轉抄,進入到朝鮮知識份子們的世界觀中,成為新的天下觀的一種。
最後,宋教授回到一個問題,「亞洲」是什麼?對於利瑪竇而言,是一個需要援引漢文語境中的「州」,得以解釋西方宇宙觀中人居世界一部的亞細亞。此時,「亞洲」一詞就成了不同文化、不同時空觀念相融合的產物。從一開始,「亞洲」就嵌入到本地文化的多樣與開放的圖景之中。然而,16 世紀以來,亞洲越來越常被想像成等級制、排他性、拼圖式的空間。但這種想像方式,自始至終卻未能徹底規訓亞洲;因為亞洲傳統也在不斷改變自身、吸收並且內化外部世界带來的空間觀念。同時,因為亞洲並未被殖民帝國徹底征服、改造,而是以多元的實踐方式,質疑單一的價值觀,以西方 (the West),發現—佔有—殖民—發展「其他地方」(the rest) 的殖民現代性論述。因此我們在今天反思所謂「現代」,是要認識到「現代」是一個全球共同參與的過程。總之借助想像亞洲的多樣而又不相互排斥的「輪廓」,能讓人類的整體空間意識更為豐留多彩。
綜合討論中,藍弘岳教授、陳正國教授、蔡偉傑教授及諸位與會學者,就地圖的繪製方式、呈現意涵與不同國家對於地圖的解讀方式與宋教授進行對話。宋教授針對上述問題,逐一回應。演講於師友們的對談中圓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