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三次討論會紀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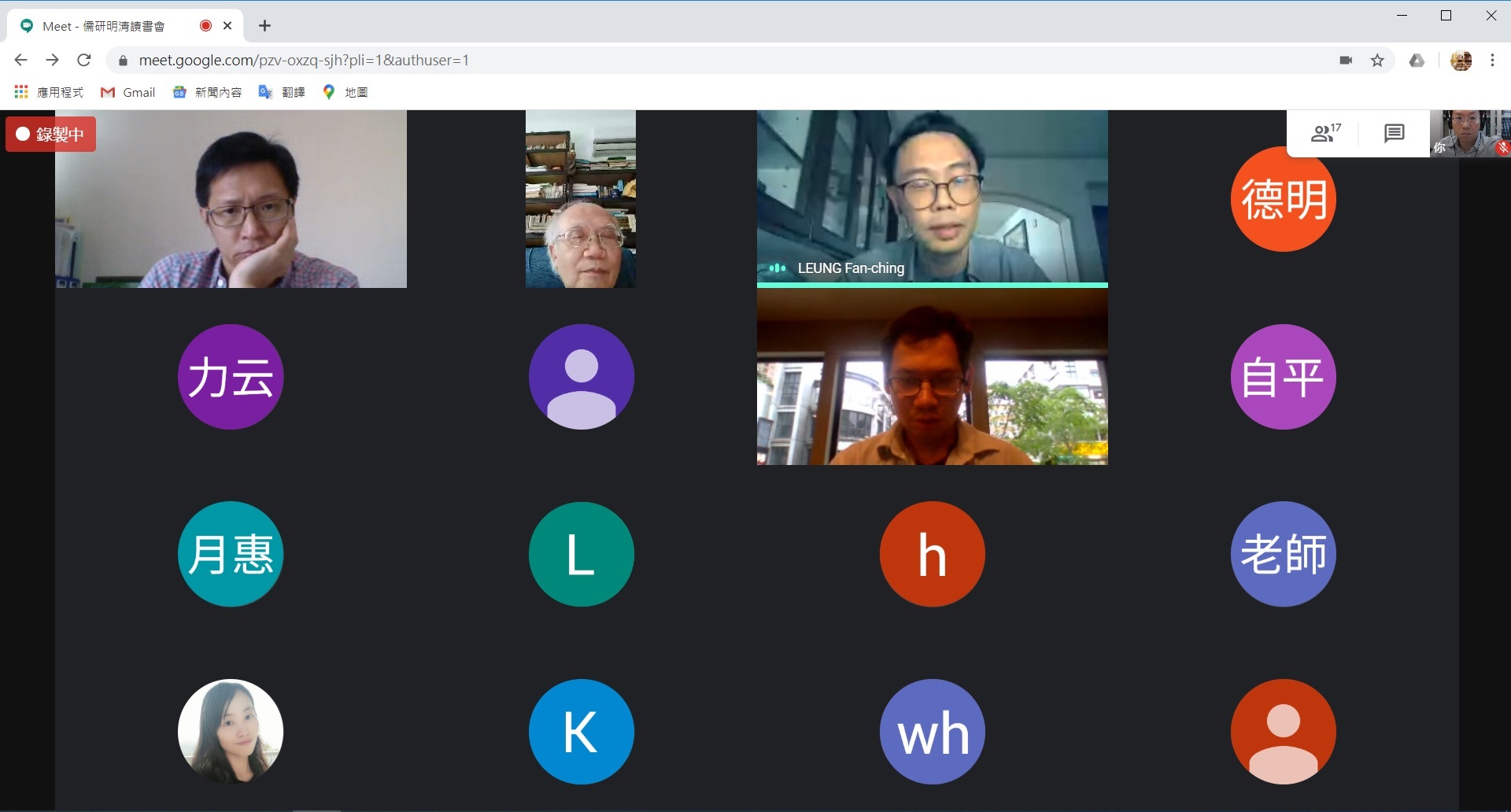
|
武億 (1745-1799) 之學為研治清代金石學、經學、考據學者所不可忽略者,特別是他通過經史考證所透顯的治經思考,頗為傳統經學家典型。王慧茹教授之作,先以傳統解經學立場說明武億的治經方法進路,鉤稽並分析其經學詮釋特徵;其次指出武億經學詮釋之特殊眼光,言其價值及限制;最後對比於現代詮釋學類型,試圖為武億經學詮釋做為一種「技藝詮釋學」之類型,提供定位及說明,指出其詮釋向度。
與會者提出幾點疑問:一、武億經學和乾嘉其他經學家,如戴震、二王,是否有更具體的方法貢獻?二、武億強調斷句,斷句是否有唯一標準?還是確實可兩從?三、武億之學和幕主、朝廷關係為何?是否可從此上觀察考慮?
王教授回應指出,一、武億強調斷句、音讀,但確實未進一步建構我們今日所知的治經理論學說,但此並不意味著武氏沒有經學理論。對比戴震、二王等,武億講的更細緻、更基礎,雖然大體上,由訓詁而義理的路子相同,但重點有別。此從他撰作《碎義》,後改名《義證》可見。二、武億解經,有些地方有判定斷句的標準,有些採並見,本文認為武億的立場模糊,但確實解經斷句也有兩從者,此牽涉經義之解釋。三、武億學無師從,學問養分都來自游幕期間累積,及與其他門幕互動而來。至於武氏和幕主的關係,本文的處理略見單薄。乾嘉幕主編書,有些是因應幕主任官治政之需,有些是幕主興好,確可就此補充。
詹秉叡教授於文中指出戴震與朱熹同,皆視孔、孟思想為儒學旨歸,不過他們眼裏的孔孟卻大相逕庭。其中,由於孔子的言論未若孟子說得豐富並且清楚,因此對於孟子思想的詮釋,更成為兩造間駁火的戰場,造成「一個孟子、各自表述」的局面。若說朱熹理學是他出入佛道後回歸儒門的所思所得,那麼戴震的學術則是其出入朱熹理學後的進一步反省。換言之,戴震的思想可以說是與朱熹理學對話下的產物,那麼要探究的是,對話的基準點是什麼?為什麼他們對於孟子的看法會如此南轅北轍?關於這一點,張壽安教授歸類出三項原因:一、即經學求理學;二、反朝廷朱學;三、戴震本人重視生養之欲的滿足;前一項貼合明末清初的「回歸經典運動」,後二項則聚焦於戴震對於孟子的詮釋。不過,所謂的「經典回歸」指涉的是六經,與孟子文本並不相類;若戴震的「回歸經典」與「孟子詮釋」二者並非分別孤立的運動,其中蘊含著有機的聯繫,那麼還須深究的是,兩者之間是以何種形式得以共處的?詹秉叡主張:孟子學作為朱熹與戴震的思想樞紐,更是為他們對於「解讀六經」的方法論上提供了依據。朱熹與戴震雖然以孔孟思想為準繩,但他們都有強烈的「回歸六經」的趨向;而他們的孟子學,則成為彼此解讀六經的最佳路徑。準此,朱熹以孟子的性善論述為起點貫通四書,並成為契會六經的依據。戴震則對朱子「解經方法」持質疑,為解構朱子的解經方法,戴震操戈入室,重讀孟子,使六經中的聖人之道收攝於其所詮釋的新孟子之下。
與會者提出主要的疑問,乃此文的基準點建立在朱熹如何看待四書與六經之間的關係,主張朱熹仍以六經為旨歸,四書乃為解讀六經的先備知識,如此則《語類》中朱熹重四書而輕六經的表述有所牴觸,故難以成立。
詹教授回應指出:朱熹《語類》中看似輕六經而重四書的立場,其實與本文並不衝突。朱熹曾指出讀六經「得效少」,更以「雞肋」譬喻學者習《易》與《詩》,對於六經看似並不友善。有趣的是,當朱子言及讀六經的缺點時,都是以讀《論語》和《孟子》作為參照。我們知道,朱子對於《易》與《詩》的重視是毫無疑問的,那要如何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宣稱?朱子並不否定「六經雖大」的前提;但是,正因為六經這麼「大」,我們要如何掌握?正如朱熹嘗於他處指出「六經浩渺,乍難盡曉」,因此我們都應該掌握「門庭」──也就是「讀書之法」。在毫無「大本」的指引下,倉皇進入六經之中與墜五里霧無異,是很難有什麼收穫的。
